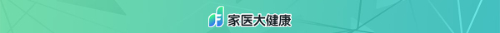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群的胆汁酸和氨基酸代谢与花生口服免疫疗法失败相关。
花生过敏是由致敏性Ara h蛋白引发的,是食物诱发过敏反应的主要原因。尽管花生口服免疫疗法(POIT)已被证明在使患者对花生脱敏方面有一定效果,但只有约20-30%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能够实现长期缓解。POIT的疗效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患者的年龄和血清中花生特异性IgE水平。为了识别POIT疗效的预测因子并探讨其机制,研究团队对IMPACT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POIT试验进行了二次分析,使用了90名儿童的纵向粪便样本,并进行了16S rRNA测序、宏基因组测序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综合多组学分析揭示了肠道微生物群代谢能力与治疗结果之间的关系。治疗前存在的五种粪便胆汁酸可预测POIT的疗效(AUC 0.71)。治疗失败与特定的胆汁酸谱、增强的氨基酸利用以及编码一种切割含脯氨酸三肽的细菌水解酶的ptpA基因拷贝数较高有关——这是花生过敏蛋白Ara h 2的一个特征。体外实验表明,在POIT未能诱导缓解的儿童粪便培养物中,Ara h 2浓度较低。因此,远端肠道微生物群的新陈代谢似乎对POIT失败起到了一定作用。
研究对象及临床试验结果
IMPACT POIT临床试验的详细设计已在之前发表。简而言之,在基线时,共有146名花生过敏儿童被纳入并随机分配(2:1)接受POIT或安慰剂治疗。经过30周的剂量递增阶段后,POIT组儿童接受了2000毫克花生粉(轻度烘烤,部分脱脂[12%脂肪]),而安慰剂组则接受了燕麦粉,持续104周(总盲法治疗期为134周)。在治疗结束时(第134周)通过双盲、安慰剂对照的食物激发试验(DBPCFC)达到5克花生粉耐受的参与者被归类为脱敏成功(D+)。无论第134周的DBPCFC结果如何,所有参与者均避免食用花生26周(避免期),并在该期结束时(第160周)通过5克花生粉DBPCFC测试的参与者被归类为处于缓解状态(R+)。
根据DBPCFC结果,IMPACT临床试验得出了三种结果组:同时实现脱敏和缓解(D+R+)、仅实现脱敏但未缓解(D+R−)、既未实现脱敏也未缓解(D−R−;图1a)。完成IMPACT试验的93名参与者中有90人提供了五个时间点的纵向粪便样本:基线(POIT启动前)、累积期结束(EoB)、中期维持(MM)、治疗结束(EoT)和避免期结束(EoA)(补充图1a和补充数据1),最终纳入本研究的样本总数为327个。参与者的基线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研究地点、抗生素使用史和共病情况见补充数据2。
图1:粪便微生物群组成和多样性与花生口服免疫疗法结果及花生过敏严重程度相关。
粪便微生物群组成与花生口服免疫疗法结果相关
完成IMPACT试验的参与者(n = 90)在POIT和安慰剂组之间并无显著年龄差异(补充图1b)。与母体临床试验中的观察一致,在POIT治疗组内,D+R+参与者明显比另外两组(D+R−和D−R−)更年轻(补充图1c)。对来自90名参与者的263份粪便样本(安慰剂,n = 73;POIT,n = 190)进行了高质量16S rRNA扩增子序列数据分析(见“方法”部分,补充图1a和补充数据1)。比较粪便细菌的系统发生多样性(α多样性)(图1b和补充图1d)和组成(β多样性)(图1e和补充数据3),发现在任何时间点上,POIT和安慰剂参与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表明POIT并未显著改变粪便微生物群组成。同样,在安慰剂和各个POIT结果组之间的成对比较中,粪便微生物群组成也没有显著差异(补充数据3)。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我们重点关注POIT组以识别治疗结果的预测因子和机制。
为了确定POIT组内的潜在混杂因素,使用基于非加权UniFrac距离矩阵的双侧PERMANOVA分析在每个时间点将临床和人口统计变量作为独立项进行检查。筛选时的年龄、样本收集日期、性别和研究地点显著影响整个试验期间各时间点的粪便微生物群组成的方差(补充数据4)。因此,后续统计分析都调整了这些协变量。POIT结果(3组;P = 0.008,R² = 0.07,n = 47)和花生过敏缓解状态(R+状态;P = 0.003,R² = 0.04,n = 47)也都与基线样本中粪便微生物群组成的方差相关(补充数据4),表明治疗前的微生物群与POIT疗效相关。
实现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粪便微生物群组成
虽然在POIT组内的三个结果组之间的纵向α多样性没有显著差异(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E];图1c),但在基线时,D+R+组的系统发生多样性显著低于D+R−和D-R-组(P = 0.001和P = 0.052;Wilcoxon秩和检验。图1d和补充图1d)。即使在调整年龄后,这一发现仍然显著(图1c,P = 0.043 ANOVA)。此外,POIT结果组的粪便微生物群β多样性也存在差异(图1f)。具体来说,与未实现缓解的参与者相比,实现缓解(D+R+)的参与者在第一主成分(轴1)上的粪便微生物群组成存在差异(D+R+ vs D+R−,P = 0.01;D+R+ vs D−R−,P = 0.004,LME;图1g)。这提供了证据表明,粪便微生物群组成和多样性与POIT结果相关。
基线细菌系统发生多样性与花生特异性IgE呈正相关,与年龄无关
在IMPACT临床试验中,较低的花生特异性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浓度在POIT启动前预示着缓解。因此,我们试图确定粪便微生物群特征是否与IgE水平相关。在调整年龄后的分析中,基线样本中α多样性与总IgE(图1h)、花生特异性IgE(图1i)和Ara h 2特异性IgE(图1j;P < 0.05 Pearson相关)水平呈正相关,表明增加的粪便细菌多样性与较高的IgE水平相关,并降低了POIT后花生过敏儿童的缓解可能性。
由于在IMPACT试验中,较年轻的年龄和较低的基线花生特异性IgE水平预测了临床缓解,我们接下来识别了与花生特异性IgE水平和缓解状态相关的基线序列变异(SVs)(调整年龄后的分析)。Romboutsia ilealis/timonensis与POIT诱导的缓解相关,而Ruminococcaceae连同Parabacteroides distasonis和Oscillospirales成员与未能发展缓解相关(P.FDR < 0.05。LME,调整年龄,图1k)。R. ilealis/timonensis还与基线时的花生特异性IgE水平负相关(P.FDR < 0.05。双侧LME,调整年龄);图1l和补充数据5)和花生及其成分(Ara h)特异性IgE水平(Ara h 1、2、3和6 IgE;补充图1e)。因此,尽管POIT并未显著影响粪便微生物群组成,但在POIT治疗期间的基线和整个试验过程中,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与治疗结果相关。此外,在花生过敏儿童中,不论参与者的年龄如何,治疗前较低的细菌系统发生多样性和特定粪便微生物成员的相对丰度与花生过敏敏感性的多个指标相关。
基线胆汁酸谱与POIT疗效相关
粪便微生物群扰动和代谢功能障碍,包括促进过敏炎症主要特征的代谢物浓度增加,是过敏疾病的特征。为了确定与POIT结果相关的不同粪便微生物群组成是否表现出不同的代谢谱,对一个子集(见“方法”部分)的参与者进行了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这些参与者在三个关键访问点提供了足够的粪便样本用于分析:基线、治疗结束和避免期结束(n = 58参与者 [POIT = 43,安慰剂 = 15],174份粪便样本;图1a,补充图1a和补充数据1)。与粪便微生物群组成一样,基线粪便代谢物谱与POIT结果组相关(n = 43,R² = 0.07,P = 0.01),更具体地说,与POIT治疗儿童的缓解状态相关(n = 43,R² = 0.04,P = 0.01;双侧PERMANOVA,欧几里得距离矩阵,补充数据6)。
为了识别与POIT结果相关的代谢物,采用了一种数据简化方法,即加权基因相关网络分析(WGCNA),以识别协同关联的代谢物模块,然后将其与POIT结果相关联。识别出50个代谢物模块(非靶向代谢物模块[UMMs];补充数据7),其中九个与POIT结果显著相关(P.FDR < 0.05,ANOVA,调整年龄,图2a和补充数据8)。这些与POIT结果相关的代谢模块主要由脂质组成,特别是胆汁酸(BA),以及氨基酸模块(AA;图2a和补充数据7)。双侧PERMANOVA分析显示,仅在基线时,BA谱在POIT结果组之间有显著差异(图2b;n = 43,R² = 0.10,P = 0.015,双侧,PERMANOVA,欧几里得距离矩阵),而在治疗结束或避免期结束时不显著(补充图2b),表明治疗前的粪便代谢状态与治疗结果最为相关。三个BA模块(UMM10、UMM15和UMM4)与治疗结果相关(图2c-e)。UMM10包含石胆酸和脱氧胆酸等其他BAs,在未能发展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中增加(图2c, f)。含有硫酸化BAs的UMM15(图2d, g),以及包含7-酮石胆酸和7-酮脱氧胆酸等其他BAs的UMM4在这些参与者中减少(图2e, h)。这些数据表明,在POIT启动时存在的特定BA谱与POIT疗效相关。
图2:基线胆汁酸谱与POIT疗效相关。
a 非靶向代谢组学模块(UMM)特征向量与POIT结果之间的关联(双侧ANOVA,调整年龄)。b 基线次级BA代谢物排序(n = 43,R² = 0.10;P < 0.015,调整年龄),基于欧几里得距离矩阵的PERMANOVA分析(双侧)。c UMM10的模块特征向量(ME)差异,这是根据WGCNA分析确定的(见“方法”部分),代表特定模块的联合丰度谱。d UMM15,和 e UMM4在POIT结果组之间的差异。双侧Wilcoxon符号秩检验(n = 129;D+R+ = 33,D+R− = 78,D−R− = 18)。数据显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箱线图显示中位数(中心线)、第25和第75百分位数(箱子边界),以及延伸至距四分位间距1.5倍范围内的值。f 每个POIT结果中UMM10的每个BA相关代谢物的基线Z分数。g UMM15 和 h UMM4。蓝色表示低z分数,即低丰度,红色表示高z分数和更高的丰度。i 在避免期结束时,POIT响应者相较于非响应者表现出更高的EC.1.1.1.392酶拷贝数(P = 0.024,双侧Wilcoxon符号秩检验;缓解,是=16,否=44)。数据显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箱线图显示中位数(中心线)、第25和第75百分位数(箱子边界),以及延伸至距四分位间距1.5倍范围内的值。j EC.1.1.1.201酶拷贝数与基线样品中石胆酸丰度呈负相关(n = 32,r = −0.35,p = 0.041。调整年龄)。线条周围的阴影区域表示拟合回归线的95%置信区间。k Bifidobacterium breve和Ruminococcus gnavus在POIT响应者中编码显著更高拷贝数的次级BA生产酶(n = 16)相较于非响应者(n = 44)。数据被过滤以保留log2倍变化超过±0.5的酶。“*”表示P < 0.05,“**”表示P.FDR < 0.05。Log2 FC (cpm)表示缓解组和非缓解组之间每百万拷贝数的Log2倍变化(双侧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红色表示缓解组中Log2 FC (cpm)增加。确切P值见补充数据12。l R. gnavus(P = 0.042)和B. breve(P = 0.027)的平均相对丰度在POIT响应者(n = 16)中显著富集,相较于非响应者(n = 44)。数据显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箱线图显示中位数(中心线)、第25和第75百分位数(箱子边界),以及延伸至距四分位间距1.5倍范围内的值。统计比较使用双侧Wilcoxon秩和检验。原始数据作为源数据文件提供。
全尺寸图像
由于BAs在早期生活中驱动肠道微生物群成熟,我们进一步调查了UMM10和UMM15 BA模块与与POIT结果相关的粪便微生物群特征之间的关系。UMM15主要由细菌衍生的次级BAs组成(补充数据7),显示出与粪便微生物群α多样性显著的负相关(较低的基线α多样性与缓解相关;图1d)和与基线微生物群组成的轴1正相关。相比之下,UMM10模块表现出相反的关系,与粪便α多样性正相关,与基线微生物群组成的轴1负相关(补充图2c)。这些数据表明,在基线时,次级BAs与较低的粪便细菌多样性和独特的粪便细菌组成相关,这些特征表征了发展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
尽管基于16S rRNA的生物标志物测序可以揭示粪便微生物群与临床结果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它基于单一基因,无法提供关于微生物组基因内容和对治疗结果的功能贡献的信息。为了识别与POIT结果相关的粪便微生物途径,包括那些导致治疗结果组之间代谢差异的途径,我们在基线(n = 75)、治疗结束(n = 54)和避免期结束(n = 55)的粪便样本上生成了宏基因组测序数据,包括所有已进行平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的样本(图1a,补充图1a和补充数据1)。与基于16S rRNA的粪便微生物群和代谢组组成类似,在POIT组内,基线时的粪便微生物组功能能力与POIT结果组相关(n = 60,R² = 0.04,P = 0.025),并且与缓解状态相关(n = 60,R² = 0.022,P = 0.0027;PERMANOVA,堪培拉距离矩阵,补充数据9)。
接下来,我们在E.C.水平上检查了粪便宏基因组,特别关注那些已知在肠道微生物BA代谢中起作用的酶,包括由细菌bai操纵子编码的7α-脱羟基酶。其中,仅有一种肠道微生物编码的BA酶,EC. 1.1.1.392(3-α-羟基胆烷脱氢酶),该酶利用石胆酸作为底物生成异BAs,在基线时显著不同(补充数据11),在POIT响应者中增加(图2i)。与增强的微生物利用石胆酸一致,该细菌基因的丰度与基线粪便样本中的石胆酸相对浓度呈负相关(图2j)。
使用宏基因组数据,我们接下来鉴定了编码BA酶的微生物物种,包括EC.1.1.1.392。值得注意的是,Bifidobacterium breve和Ruminococcus gnavus表现出更高拷贝数的参与BA代谢的酶。这些酶包括胆酰甘氨酸水解酶(EC. 3.5.1.24,P.FDR < 0.05)和与异BA生产相关的酶(EC. 1.1.1.392,EC. 1.1.1.393)以及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EC. 1.1.1.201,P < 0.05但P.FDR > 0.05,LME)在实现POIT诱导缓解的患者中(图2k和补充数据12)。使用Kraken2进行的分类分析进一步显示,B. breve和R. gnavus在POIT响应儿童中显著富集(图2l)。这些发现表明,POIT响应者和非响应者之间不同的粪便BA组成是由POIT响应患者增强的微生物BA代谢能力驱动的。
治疗前选择性胆汁酸的丰度预测花生口服免疫疗法的结果
我们接下来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参与者的基线粪便样本中五个最重要的代谢物进行了逻辑回归分析。这五个代谢物在基线时的粪便丰度具有中等的预测能力(从重复100次的五折交叉验证得出的曲线下面积[AUC],以平均AUC ± 标准差[s.d.]表示:AUC逻辑回归:0.712 ± 0.081;图3d)。为了验证我们的发现,应用了第二种机器学习模型,即随机森林模型,表现相似(补充图3e和补充数据13)。
在这些预测性BAs中,7-酮脱氧胆酸和7-酮石胆酸分别由脱氧胆酸和石胆酸生成,这两者在POIT响应者中均被耗尽。依赖NADP+的肠道微生物EC. 1.1.1.20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7b-HSDH)酶在这条途径中起关键作用。该基因的拷贝数也在实现缓解的粪便微生物组中显著富集(P < 0.05,图2k),并与7-酮脱氧胆酸和7-酮石胆酸次级BAs的丰度呈正相关(图3f, g,P < 0.05;Pearson相关)。总体而言,我们的数据表明,治疗前粪便中某些BAs的浓度,包括7-酮脱氧胆酸和7-酮石胆酸,代表了治疗反应的有用预测因子,并识别出负责其生产的特定肠道细菌和酶。
增强的微生物组蛋白代谢与POIT失败相关
四个与POIT相关的代谢物模块(UMM4、UMM5、UMM7和UMM50)主要由AAs组成(图2a和补充数据7)。这些模块的丰度在POIT未能诱导脱敏和/或缓解的儿童中显著降低(图2e和图4a)。值得注意的是,POIT结果组之间的AA谱在基线时显著不同(n = 43,R² = 0.08;P = 0.006,图4b)和避免期结束时显著不同(n = 43,R² = 0.07;P = 0.039,图4c),但在治疗结束时不显著(双侧PERMANOVA分析,补充图3f),表明较低的饮食AA摄入和/或治疗期间增强的微生物AA代谢区分了那些是否发展POIT相关缓解的个体。
图4:增强的微生物组蛋白代谢与花生口服免疫疗法失败相关。
a POIT结果组之间UMM5、UMM7和UMM50 AA模块的模块特征向量差异(n = 129;D+R+ = 33,D+R− = 78,D−R− = 18)。数据显示为平均值 ± 标准误。箱线图显示中位数(中心线)、第25和第75百分位数(箱子边界),以及延伸至距四分位间距1.5倍范围内的值。统计比较使用双侧Wilcoxon秩和检验。b 基线时POIT结果组之间的粪便AA代谢物组成显著不同(n = 43,R² = 0.08;P = 0.006),和c 避免期结束时(n = 43,R² = 0.07;P = 0.041)。PERMANOVA分析(双侧)基于欧几里得距离矩阵。d 与POIT结果相关的九个模块中所有AA代谢物丰度的Z分数。e 在避免期结束时,POIT响应者的粪便微生物组中ptpA基因拷贝数较POIT非响应者升高(P.FDR < 0.05,调整多次比较的双侧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确切的P值见补充数据15。f ptpA基因拷贝数与基线时的Ara h2特异性IgE水平正相关(n = 57,p = 0.004,R² = 0.37),g 治疗结束时(n = 39,p = 0.0004,R² = 0.53)和h 避免期结束时(n = 35,p = 0.05,R² = 0.32)。双侧Pearson相关。i 未能实现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粪便微生物组显示出比实现缓解的儿童更大的降解花生Ara h 2蛋白的能力(P = 0.032)。所示的Ara h 2浓度是每个样本两次独立实验的平均值。每个数据点代表一个生物学独立的参与者(缓解 n = 6,未缓解 = 12),并使用双侧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比较。箱线图显示中位数(中心线)、第25和第75百分位数(箱子边界),以及延伸至距四分位间距1.5倍范围内的值。统计比较使用双侧Wilcoxon秩和检验。对照组指添加了花生提取物并在厌氧条件下孵育48小时的BHI培养基样本,与其他未接种微生物组的样本一起孵育。BA:胆汁酸。AA:氨基酸。原始数据作为源数据文件提供。
全尺寸图像
四个POIT反应相关的代谢物模块(UMM4、UMM5、UMM7和UMM50)总共包含87个AAs及其衍生物,其中68个属于UMM4(补充数据7),在D−R−组中显著减少(图2e)。在未能实现缓解的儿童粪便中,多数这些AA代谢物的丰度相对浓度降低(图4d)。值得注意的是,在未能实现缓解的两组(D+R−和D−R−)中,微生物衍生的支链AA发酵终产物如粪臭素和吲哚的浓度增加,表明治疗失败可能部分是由于微生物AA利用的增加。
AAs是厌氧肠道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并且某些微生物能够通过去结合初级BAs来获取AAs以支持核心代谢。粪便AA浓度的降低(图4d)和厌氧能量和糖异生代谢的增加(图3b)促使我们研究其粪便微生物组是否编码了独特或增强的AA或蛋白质利用能力。使用纵向微生物途径丰度数据,我们发现L-组氨酸降解、厌氧能量代谢、L-瓜氨酸生物合成(精氨酸降解)和糖异生(使用包括AA在内的非碳水化合物来源进行能量生产)途径在未能实现缓解的儿童粪便微生物组中富集。相比之下,实现缓解的儿童拥有富含AA生物合成途径的粪便微生物群(LME,P < 0.05,但P.FDR > 0.05;补充图3g和补充数据14)。此外,在我们的综合MOFA2分析中,因子3显著区分了D+R+组与D+R−和D−R−组(补充图3b);L-酪氨酸和L-色氨酸生物合成途径是该因子前五位贡献者之一(补充图3c)。这些数据表明,具有增强的糖异生和AA代谢能力的微生物组与粪便AA代谢物的耗竭相关,这是未能实现花生过敏缓解的POIT治疗儿童的特征。
在每个时间点的微生物酶差异丰度分析中发现,只有ptpA基因在避免期结束时在POIT响应者和非响应者之间显著不同(LME,log2倍变化≥ |1|,P.FDR < 0.05)。在其他时间点没有其他微生物酶达到显著性(补充数据15)。未能发展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中,ptpA基因的拷贝数增加,这是一种切割第三位置具有脯氨酸残基的N端三肽的水解酶。ptpA基因拷贝数与几个模块相关,包括UMM7 AA(双侧Pearson相关,R² = −0.26;P.FDR = 0.058)和UMM10次级BA(双侧Pearson相关,R² = 0.28;P.FDR = 0.058)模块(补充数据16)。
Ara h 2是最具致敏性的花生蛋白成分,包含六个脯氨酸残基。在非响应儿童的粪便微生物组中,我们发现ptpA基因主要由Bacteroides物种编码,包括B. dorei、B. uniformis、B. caccei和B. xylanisolvens(补充图3h)。因此,我们测试了ptpA基因拷贝数与IMPACT试验中接受POIT的参与者的Ara h 2特异性IgE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并在基线(图4f)、治疗结束时(图4g)和避免期结束时(图4h)发现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些数据表明,未能实现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粪便微生物组具有增强的代谢含脯氨酸蛋白质的能力,这可能扩展到对蛋白酶抗性较强的Ara h 2蛋白质的降解,从而减少了对这种关键花生抗原的暴露。
LEAP临床试验清楚地证明了花生暴露对发展免疫耐受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假设未能诱导POIT缓解的儿童粪便微生物组具有增加的花生蛋白降解能力,从而有效减少抗原暴露。为了测试这一点,按照先前描述的方法开发了来自每个结果组的稳定体外粪便微生物组培养物,并在厌氧条件下与花生提取物共孵育48小时,随后通过ELISA量化Ara h 2浓度。无论缓解结果如何,所有参与者的粪便微生物组表现出降解Ara h 2的能力,这是一种高度抵抗蛋白酶解的花生蛋白抗原。此外,与实现缓解的儿童相比,未能实现缓解的患者的花生孵育物显示出显著降低的这种抗原浓度。这些数据表明,未能实现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粪便条件促进了Ara h 2蛋白的降解,从而内在减少了对这种关键花生抗原的暴露(图4i)。
讨论
对90名IMPACT参与者(安慰剂,n = 23;POIT,n = 57)纵向收集的粪便样本进行微生物组分析,提供了微生物组组成、功能和代谢活动与POIT结果相关的证据,并且这些关系在治疗开始前最为明显和强烈。尽管在整个试验过程中,POIT和安慰剂组之间的粪便细菌多样性和整体组成相似,但在POIT组内,三年治疗期内粪便微生物群组成和功能能力在实现或未实现花生过敏缓解的个体之间显著不同。包括在基线样本中富集的次级BAs在内的BAs与POIT诱导缓解相关,并似乎是治疗结果的合理预测因子。鉴于POIT疗程较长且在治疗花生过敏人群中严重不良事件风险较高,利用粪便生物标志物在治疗开始前测试治疗反应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最近的一项报告一致,该报告显示在较小队列的20名儿童中,血浆BAs与花生口服免疫疗法的疗效相关。
肠道微生物衍生的次级BAs作为调节胆固醇代谢、脂质和可溶性维生素摄取的激素,并通过核受体和G蛋白偶联受体影响能量平衡,从而塑造先天免疫反应。先前的研究表明,BA池调节表达转录因子RORγ的结肠FOXP3+调节性T细胞。实际上,在IMPACT试验参与者的亚分析中,Calise及其同事检查了花生挑战患者的T细胞谱系,发现脱敏患者的调节性T细胞功能相关基因表达趋势增加,与未能实现脱敏和缓解的患者相比。
肠道微生物能够代谢膳食蛋白质,利用宿主和膳食氨基酸(AAs)进行蛋白质合成,并从初级BAs中获取AAs以支持核心代谢。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POIT未能诱导缓解的儿童,其肠道微生物群特征为增强的微生物AA利用途径、AAs及其代谢物的耗竭以及特定去结合次级BA代谢物的富集。初级BAs,如甘氨胆酸和牛磺胆酸,通常与甘氨酸和牛磺酸结合,尽管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更广泛的AAs可能被结合。初级BAs被结肠细菌转化为免疫调节次级BAs。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初级BAs,特别是鹅去氧胆酸,可以通过激活树突状细胞中的视黄酸反应元件,驱动食物过敏原特异性IgE和IgG1的产生。增强的肠道微生物群从结合型BAs中获取AAs的能力可能会提高去结合型BAs的水平,从而促进过敏免疫功能并导致POIT失败。
先前的研究已经建立了生命第一年内受损或延迟的微生物群多样化与儿科过敏症发作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数据表明,婴儿期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群对于适当的免疫发育和预防过敏疾病至关重要。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较大的花生过敏儿童中,那些实现POIT诱导缓解的儿童表现出显著较低的基线微生物群多样性,与POIT未能诱导缓解的儿童相比。这一观察结果似乎与现有文献相悖。然而,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高风险过敏疾病的婴儿在生命的第一年内最初表现出比低风险婴儿更低的粪便多样性,但在18到24个月龄时,粪便多样化的交叉事件发生,前者表现出持续多样化,而后者达到平台期。这些数据表明,虽然婴儿期较低的粪便多样性是走向过敏轨迹的一致特征,但在较大儿童中,较高的粪便多样性是疾病风险增加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机制。非缓解相关特征,如AA营养缺陷(即无法合成生长所需的AAs),之前已被证明与更高的微生物群多样性相关,因为微生物依赖于外源AA来源。此外,我们表明粪便BA谱与花生过敏儿童的微生物多样性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表明BA池和多样性调节肠道微生物组成和功能。
先前的研究报道,Clostridia成员,包括R. gnavus,与食物过敏的发展相关。这种物种的丰度与年龄正相关,并且已知能够产生免疫调节次级BAs。在IMPACT试验中,发展POIT诱导缓解的参与者拥有更大丰度的R. gnavus。这些菌株编码了几种与疾病缓解相关的特定BAs的酶,表明菌株特异性BA代谢能力而非仅仅是物种相对丰度对食物过敏临床结果至关重要。事实上,R. gnavus菌株的代谢能力是巨大的;先前的研究表明,来自食物过敏儿童的菌株编码减少了纤维素降解能力和与促炎多糖生产相关的基因,使其与非过敏对应物的菌株区分开来。这些发现强调了评估食品过敏表型背后菌株解析功能差异的必要性。
食物过敏和不耐受通常由食物中的特定蛋白质模体触发,例如花生中的Ara h蛋白、牛奶中的酪蛋白和β-乳球蛋白以及贝类中的原肌球蛋白。摄入的过敏原在口腔、胃和小肠中经历酶促分解,然后与抗原呈递细胞相互作用。然而,某些关键的抗原性花生蛋白,例如Ara h 2,高度抵抗蛋白酶解,很可能通过上消化道到达远端结肠,那里有着最高密度的微生物和免疫细胞,包括T和B效应细胞。花生蛋白的消化程度决定了可用于抗原呈递细胞呈现的抗原性花生肽的浓度和谱系,这是发展免疫耐受的关键要求。远端肠道定植着一群复杂的代谢活跃微生物,能够代谢膳食蛋白质,包括食物过敏原。我们的数据表明,增加的粪便微生物肽酶活性、花生蛋白降解和在花生引入期间选择性免疫调节BA和AA的耗竭与治疗失败相关。先前的研究表明,随后发展为特应性疾病或哮喘的婴儿的无微生物粪便提取物在体外促进典型过敏炎症特征,表明粪便代谢物足以驱动过敏炎症。我们最近的工作显示,一个预测特应性的粪便微生物衍生脂质,12,13 di-HOME,通过促进巨噬细胞表达IL-1β、TNFα、NFkB和IL-6,扩展记忆B细胞并增加花生刺激共培养中IgE与IgG的比例,加剧了对食物过敏原(包括花生)的炎症反应。因此,新兴数据指向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型,在该模型中,抗原刺激发生的代谢环境决定了功能性免疫反应,表明影响抗原可用性和免疫调节代谢物的微生物过程在决定过敏结果中起关键作用。
阐明肠道微生物对抗过敏
食物蛋白的影响,可能为开发更有效的免疫治疗方法铺平道路,既可以针对肠道微生物组的代谢功能,也可以通过例如将它们封装在食品级胶体系统中来保护免疫治疗用的花生蛋白免受微生物代谢。目前正在进行几种临床试验测试类似的封装系统用于谷蛋白免疫治疗,迄今为止已显示出安全性和有效性。我们的研究强调了肠道微生物组在塑造POIT疗效结果方面的潜在作用,并建议特定的粪便BAs可以作为识别POIT最有可能成功的个体的预后生物标志物,还可以作为提高POIT诱导缓解率的治疗靶点。
(全文结束)